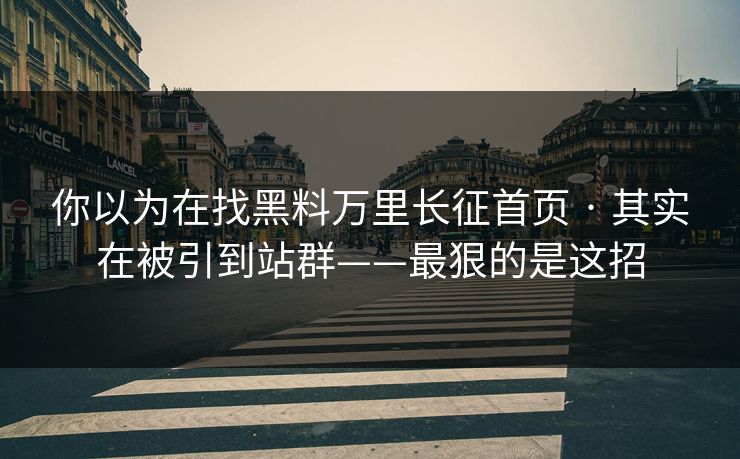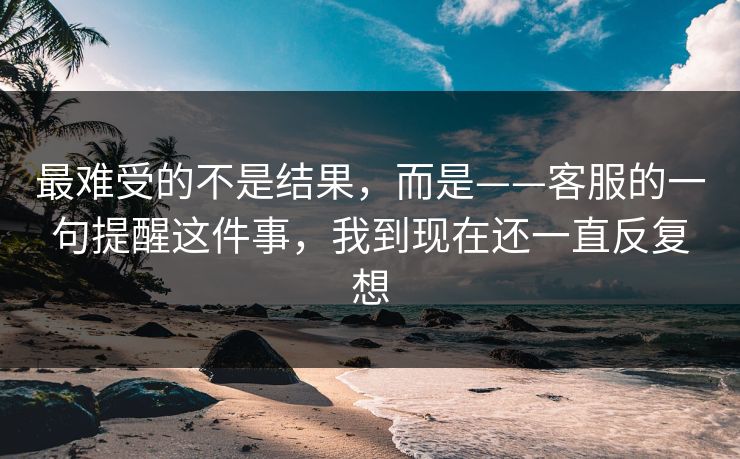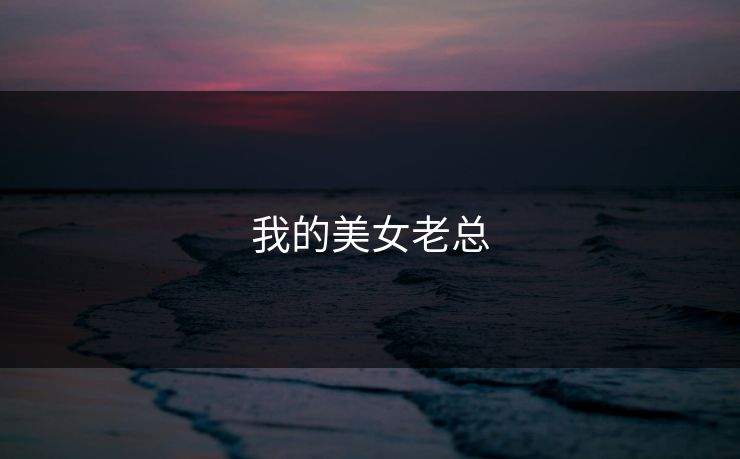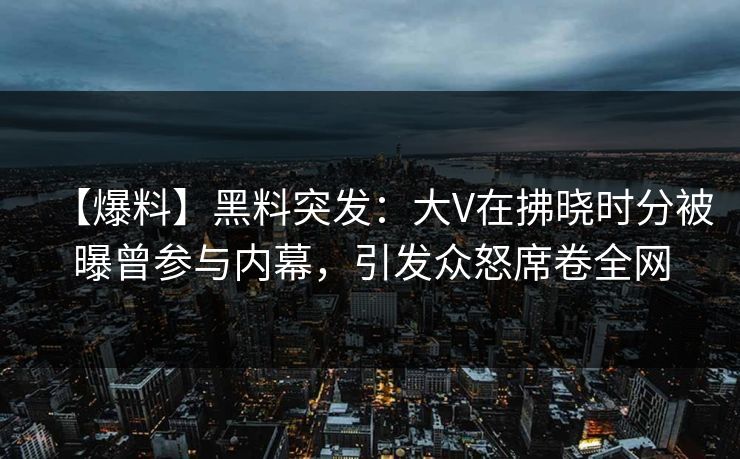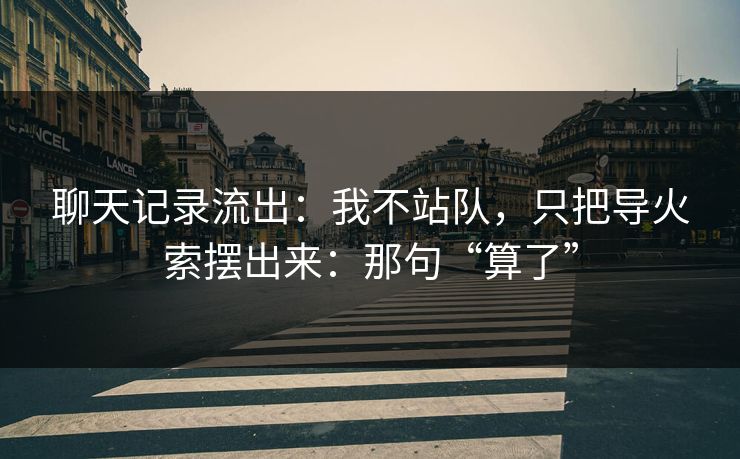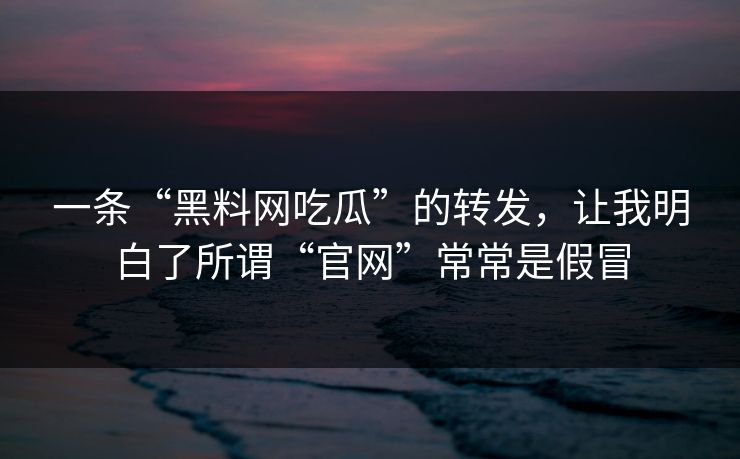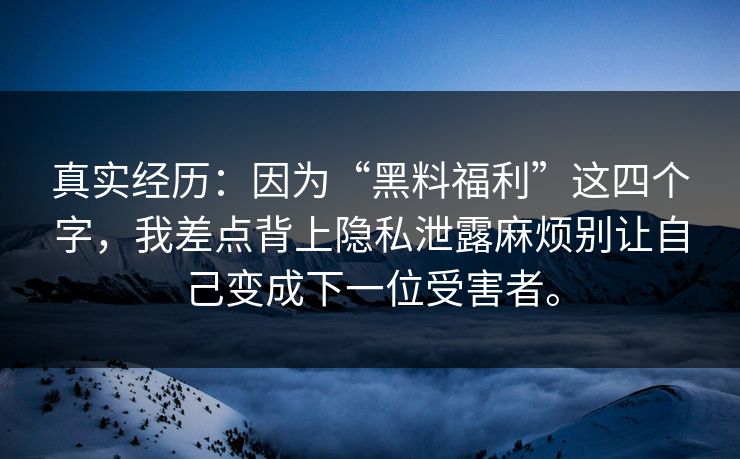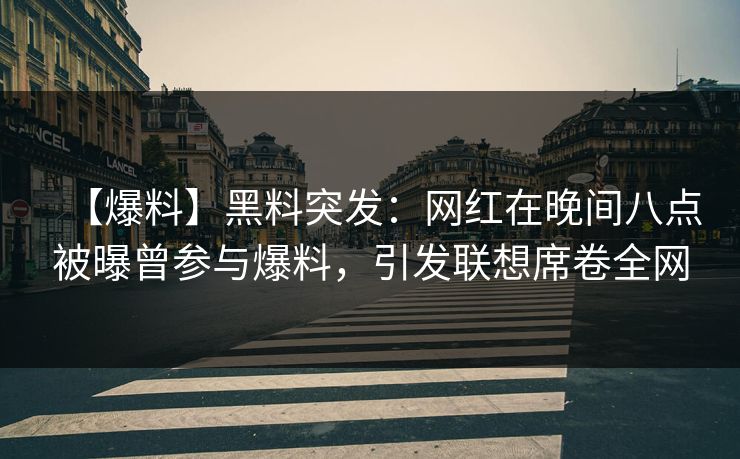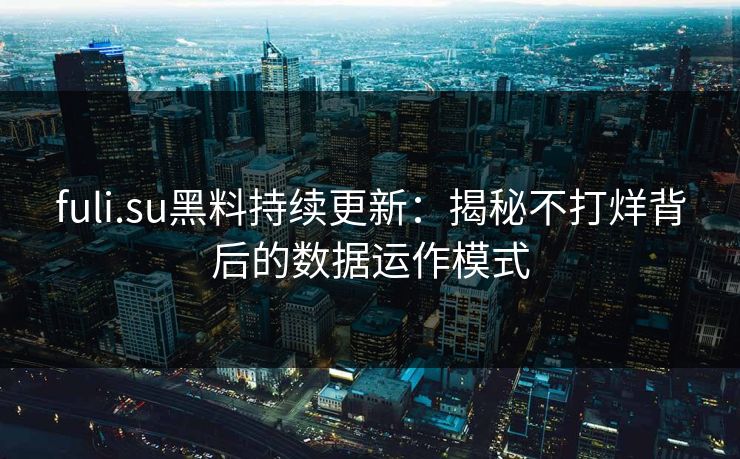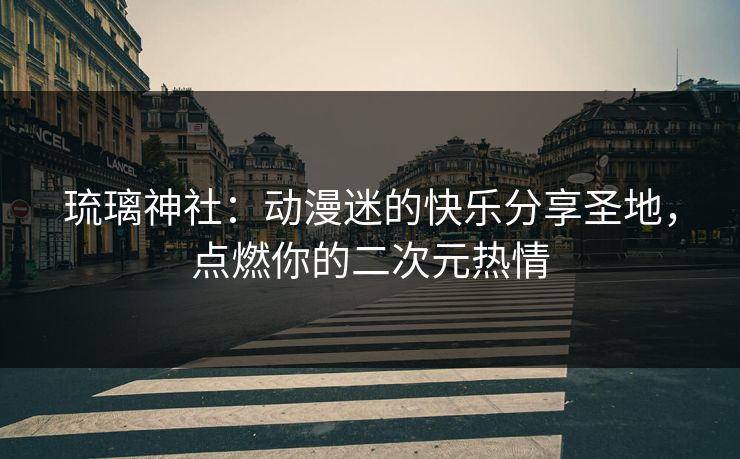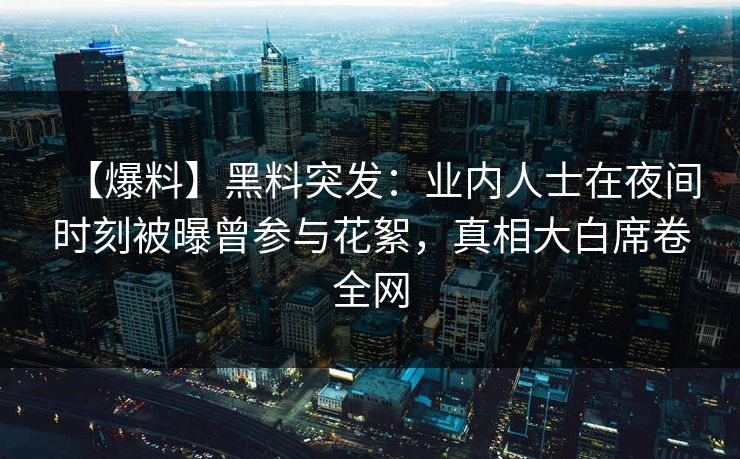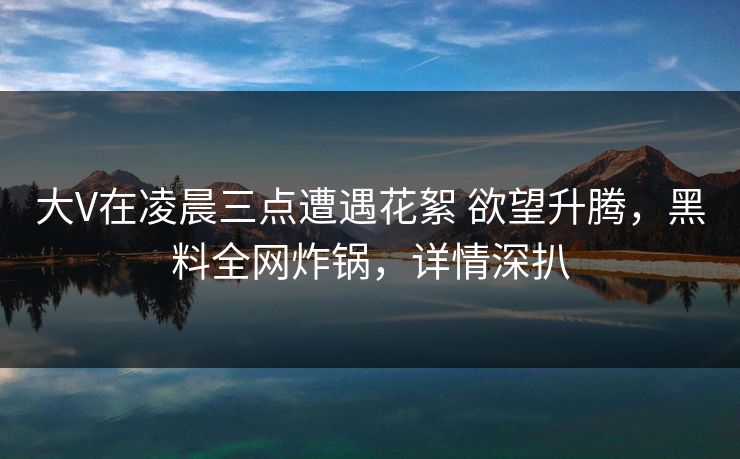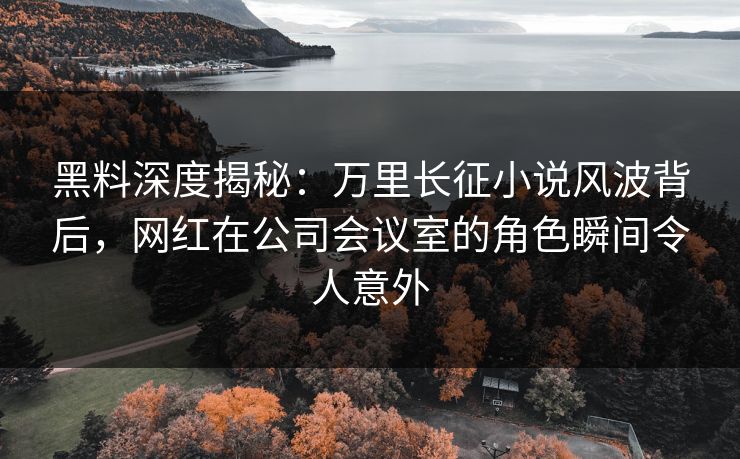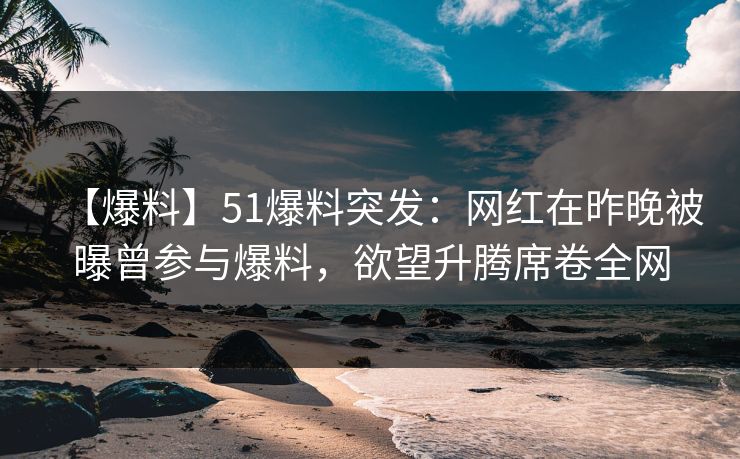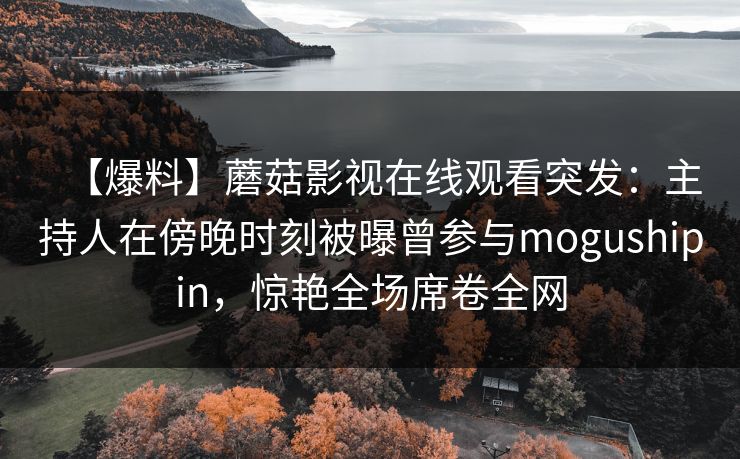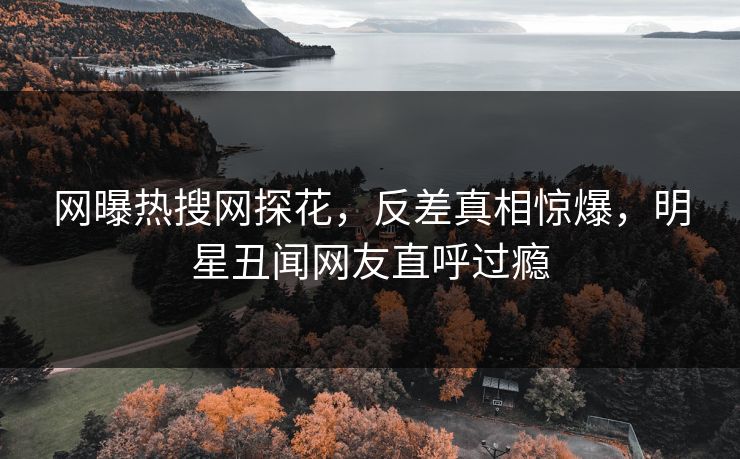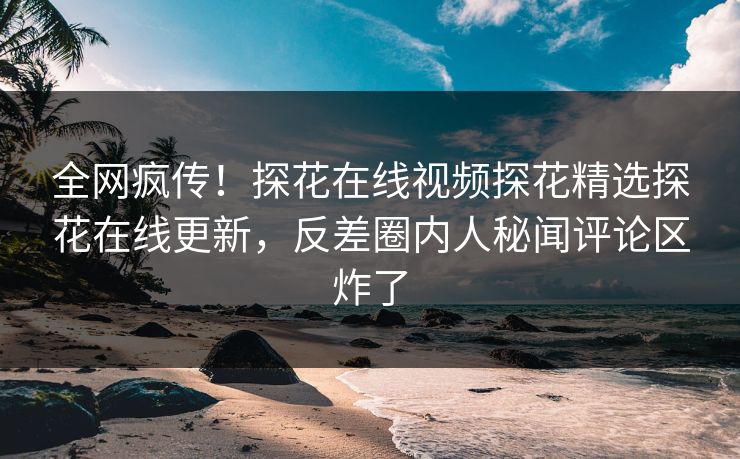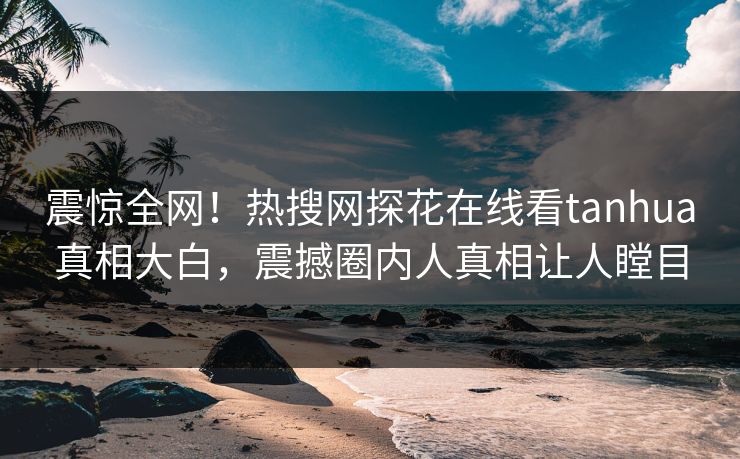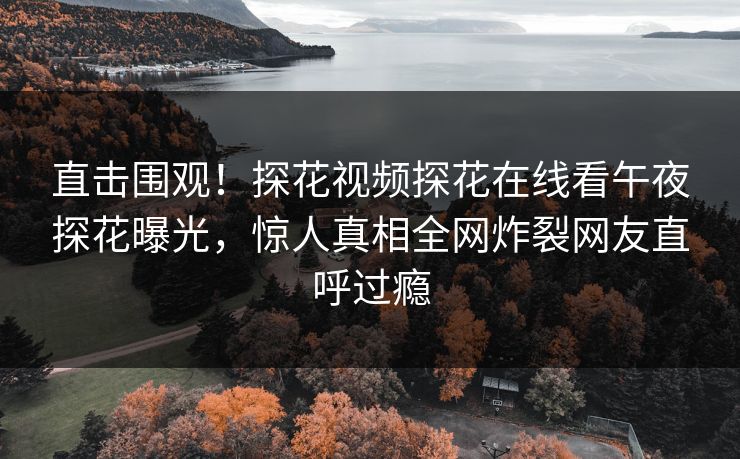新版金银瓶1996第二级:情欲与时代的隐秘对话
【欲望浮世绘:镜头下的红尘迷局】
1996年的香港,霓虹闪烁的夜色中悄然诞生了一部注定被争议缠绕的作品——《新版金银瓶1996第二级》。这不是对古典文学的简单复刻,而是一场用现代视觉语言解构人性欲望的大胆实验。导演用暧昧的光影与富有张力的构图,将《金瓶梅》中那个充满权谋与情欲的世界,投射在九十年代香港的浮世绘中。

影片开篇即以一场精致的宴会戏拉开帷幕:水晶吊灯下流转的眼波,酒杯碰撞间暗藏的机锋,丝绸旗袍包裹的曲线若隐若现。这些镜头语言并非单纯追求感官刺激,而是刻意营造出一种浮华易碎的末世氛围。当杨思敏饰演的潘金莲赤足走过铺着波斯地毯的长廊时,摄像机跟随她的足踝缓缓移动,仿佛在暗示这个角色既是欲望的化身,也是被物化的囚徒。
这种视觉隐喻恰恰呼应了九十年代香港社会在回归前夕的集体焦虑——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,转化为了对当下感官体验的极致追逐。
值得玩味的是,影片将原著中的市井生活细节进行了现代化重构。西门庆的生意场变成了股票交易所,王婆的茶坊化作高端会所,就连武大郎的炊饼摊也以夜市大排档的形式出现。这种时空移植让古典文本与当代观众产生了奇妙的共鸣:原来人性的贪嗔痴慢疑,从未因时代更迭而改变分毫。
导演甚至在第二级剧情中加入了金融危机的背景设定,让西门庆的财富帝国与香港股市的起伏形成镜像——情欲与金钱从来都是权力游戏的一体两面。
影片的情欲场面处理更是独具匠心。不同于普通三级片的直白呈现,导演采用了大量象征手法:摇晃的烛影隐喻心旌摇曳,破碎的瓷器暗示道德崩解,甚至用一场暴雨中的戏码来外化人物内心的汹涌澎湃。这些设计让情欲超越了肉体层面,成为了解读人物命运的关键符号。当潘金莲在镜前梳妆的段落持续了整整三分钟时,观众看到的不仅是美人的顾影自怜,更是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自我物化与觉醒之间的挣扎。
【红尘启示录:超越情欲的人性叩问】
若只将《新版金银瓶1996第二级》视为情欲片,便辜负了创作者的深意。影片后半段逐渐剥离香艳的外衣,展现出对人性深渊的严肃叩问。当西门庆在财富巅峰突然吐血倒地时,镜头没有聚焦于他的痛苦表情,而是转向窗外熙攘的街市——个体的毁灭与世界的运转形成冰冷对比,这种存在主义式的诘问让影片获得了超越类型的哲学重量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潘金莲角色的重塑。相较于传统解读中的"淫妇"标签,1996版赋予了这个角色更复杂的心理维度。她与武松的对峙戏被改编成一场关于阶级与性别压迫的辩论:"你憎恶我的放荡,又何曾看见我被典当的命数?"这句原创台词撕裂了道德审判的表象,暴露出封建社会中女性作为交易品的本质。
而她在西门庆灵堂前焚毁账本的举动,更像是一场迟来的自我救赎——烧掉的不只是金钱契约,更是套在自己身上的无形枷锁。
影片的服装美术也暗藏玄机。潘金莲前期穿着艳丽的玫红与金色,后期逐渐转为素白与墨黑;李瓶儿的服饰始终保持着柔和的淡粉与浅紫;而孟玉楼则永远一袭青衣。这些色彩语言构建起一套视觉符号系统:红色代表被物化的欲望,粉色象征被迫的柔顺,青色则是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视角。
这种细腻的视觉叙事让影片在香艳表象下,藏着值得反复品味的艺术深度。
结局处理尤其值得称道。没有采用传统的大团圆或善恶有报套路,而是让幸存者们各自走向不同的命运轨迹:有人皈依佛门,有人远走南洋,有人成为新时代的投机者。最后一个长镜头扫过空荡荡的西门府邸,阳光透过雕花窗棂落在积尘的案几上,仿佛在说一切欲望终将归于尘土,唯有故事代代相传。
这种留白式的终结,让观众在感官刺激之后陷入更深沉的思考——我们嘲笑着片中人的荒唐,又何尝不是在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深渊?
《新版金银瓶1996第二级》之所以历经二十余年仍被影迷反复讨论,正因为它完成了情欲片最难能可贵的升华:用最世俗的题材,叩问最本质的人性命题。当剥开那些惹人非议的表象,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特有的大胆与深刻,是一群电影人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精准平衡,更是一面映照出人类永恒欲望的青铜镜。